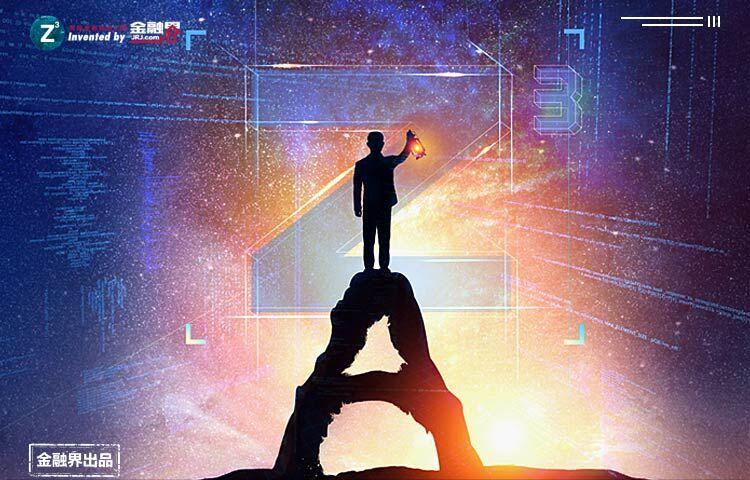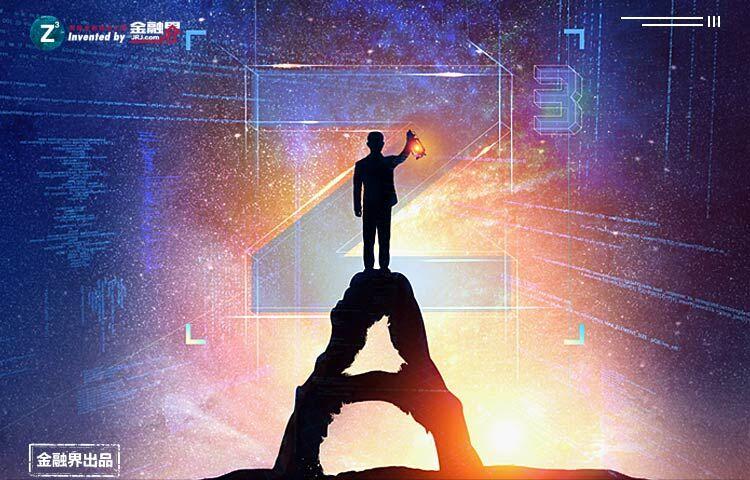馬丁·沃爾夫是《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員,他在文章中指出,雖然很多技術官僚希望能把特朗普的行為包括得更為合理化,但是到底如何實現所需的宏觀經濟調整,卻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上周,我嘗試為特朗普政府的國際經濟政策辯護,而這種做法被一些人譴責為“理性粉飾”。換句話說,我在探討,這屆政府中包括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在內的一些人提出的主張,是否具有邏輯基礎和證據支撐。
注,斯蒂芬·米蘭的《 重塑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主要內容是說美國在當前全球貿易體系中因美元長期高估而面臨制造業競爭力下降、貿易赤字擴大等結構性問題。特朗普政府若連任,可能推動通過關稅與匯率政策重構國際貿易秩序,以提高美國制造業競爭力、增強財政收入,並要求貿易與安全盟友共同分擔全球體系的成本。該文強調,通過漸進式關稅、分級制度與金融市場協調,可以在不破壞美元儲備地位的前提下,重塑全球貿易規則,實現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的雙重目標。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布拉德·德龍反駁說,這並不重要:“要達成協議,你的對手必須認為你講信用。特朗普每天都在證明自己不是那樣的人。”
我同意——而且我也表達過這個觀點。

不過,我們仍然可以追問,這里面是否存在重大政策問題,如果有,那該怎麼辦。
財政部長貝森特本月早些時候說,除了提供全球安全外,“美國……還提供儲備資產,承擔首尾消費者的角色,並在其他國家國內需求不足時吸收多餘供給。這個體系無法持續”。
米蘭也表示,美元長期被高估,“這嚴重打擊了美國制造業,而有利於經濟中金融化程度較高的部門”,最終讓富裕美國人受益。
米蘭的出發點。是羅伯特·特里芬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觀點,即全球對外匯儲備的需求導致美元被高估,並帶來了貿易和經常賬戶赤字。但這並不是各國積累外匯儲備的唯一方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莫里斯·奧布斯特費爾德,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博客中指出,外國人可以用其他外國資產替代美國資產。
此外,儲備也並不是外國人購買美國資產的唯一原因。保羅·克魯格曼也指出,他們可能只是想要美國資產。
盡管如此,儲備需求在全球收支平衡中,有時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1999年到2014年之間,全球外匯儲備總額增長了將近七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新興經濟體希望在未來避免金融危機。但就全球最大持有者中國而言,也反映了中國希望為過剩儲蓄尋找出口,並推動以出口為導向的制造業增長。
同時,特朗普政府的另一個批評對象歐元區,從1999年底到2024年底,儲備僅增加了720億美元。
一些比積累儲備更基本的力量也在發揮作用,那就是各國儲蓄和投資傾向的差異。一些國家儲蓄多於投資,因此會出現經常賬戶順差和對應的資本賬戶赤字,反之亦然。
這不一定是問題。但問題可能會出現。其中之一是,這種在全球範圍內調配資本的體系可能會引發危機。而只有那些本幣被視為可信儲備貨幣的國家,才能安全地應對這些危機。
這正是為何新興國家政策制定者通常希望保持經常賬戶順差。
另一個原因是,保持順差的國家,通常也會生產超過本國消費的可貿易商品和服務,反之亦然。所以,中國、德國和日本這些高儲蓄率國家,擁有較大制造業部門也就不足為奇。而美國和英國則處於相反的位置。盡管對於後者來說,還有一個原因是擅長服務出口,這減少了對制造品的出口。
總的來看,那些癡迷於制造業的國家往往也對順差高度執着,是典型的重商主義者。所以,這屆政府中的重商主義者,包括特朗普,並不是完全錯了:如果美國有經常賬戶順差,制造業確實會更大一些。
但他們錯就錯在,把這一切簡單歸結於外匯儲備問題。他們也沒有認真對待這種再平衡所需的條件。
如果美國要在不犧牲投資的前提下消除經常賬戶赤字,必須將儲蓄率提高至少3%的GDP,約8500億美元。這相當於財政赤字的大約一半。
正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金伯利·克勞辛所說,平均征收50%的關稅,若以最大化財政收入為目標,可以帶來每年7800億美元的收入(也就是說,不是為了保護產業,純是為了收錢,不分產品不分國家,平均一律征收一半的稅),理論上可以每年為聯邦政府帶來7800億美元的關稅收入。。
理論上,這樣的關稅能改善美國的貿易條件,主要是通過降低進口商品的相對價格來實現。
但這會帶來累退性影響(一個經濟學和財政學中的概念,指的是某項政策、制度或措施對低收入群體的負面影響大於高收入群體,也就是收入越低,所承受的相對負擔越重),對全球和美國經濟都會有負面作用,包括損害有競爭力的美國出口商。
況且,特朗普顯然對這種全面政策毫無興趣。
所以,問題依然存在:特朗普手下的技術官僚究竟如何設想實現所需的宏觀經濟調整?
他們目前提出的方案不成熟。比如,強制將外部持有的公共債務轉換,以及貶值政策,除非目的是利用通脹稅,否則這些毫無意義。
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嘗試過這種做法,結局很糟糕!
注,這應該指的是通過貶值美元、制造通貨膨脹來削減債務或調整國際收支失衡的做法,也就是所謂的“利用通脹稅”,但是後來造成了通脹失控,1979年通脹率高達13%以上,美聯儲主席沃爾克被迫在1980年代初將聯邦基金利率提高到20%,以壓制通脹,最終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衰退。
更關鍵的問題是:這樣做到底是為了什麼?
確實,如果能夠消除經常賬戶赤字,制造業會略有擴張。但從安全或其他更深層目標出發,那些真正重要的制造業部分,不一定是增長的部分。而且,沒有任何措施能夠阻止制造業就業份額的長期下降。制造業正像農業一樣,隨着生產力上升而萎縮。
即便是經過最複雜包裝的版本,“特朗普經濟學”也毫無意義且邏輯混亂。
現實版的“特朗普經濟學”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