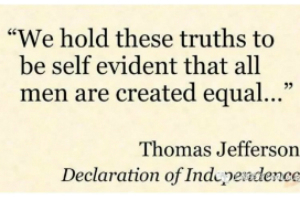雨果的小说“一七九三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革命军包围了盘踞在古堡中保王党。保王党准备从地道撤走时,房子失火了,眼看古堡中的一个寡妇三个孩子要被葬送火海了,保王党的头从地道里退回来,放弃自己逃生的机会,救了这家人。革命军看到这家人得救了,他们高喊着“国王万岁”冲了上去。故事顺着这个情节展开,笔者的话题则要定格在这个场景上。
革命军的使命是把国王送上断头台,但是,他们表达欢乐的口号却是“国王万岁”。表面的自相矛盾,隐含着内在逻辑的必然。打倒国王是革命军的理性要求,表达欢乐则是他们的感情宣泄,感情表达方式滞后于理性要求,于是只能借用过时的口号了。滞后理性的要求的不仅有感情,更有理性的其它部分。因为理性思考不会齐头并进,而像岩浆下行,各部分流动快慢的差距很大。诚如我国目前的改革,虽然确定要建设公民社会,但是,还有很多提法与这个目标并不一致。譬如,领导最喜欢说的,公众也最乐意接受的莫过于“藏富于民”了。比较历史上对公众牺牲和奉献的太多要求,“藏富于民”有了极大的进步,它可以较好地维护和满足了公众的利益和诉求。但是,就像“国王万岁”一样,“藏富于民”也不符合共和国理念与公民意识。
藏富于民or还之与民是个两千多年前就讨论的难题
任何话语的含义不仅在于它的字面,更在于它的话语背景。中国历史上“藏富于民”做的最好的莫过于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和康乾盛世,在那些朝代,所有的财富都属于皇帝和朝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按照这样的话语背景,“藏富于民”就是将朝廷皇帝的财富放在公众这里。与共和国理念的矛盾正在于此。因为共和国按照“财富”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的原则构建,所以共和国的“财富”不是国家的,不是政府的,而是公民的。顺着这样的思路,当政府把财富给予公众时,就不是“藏富于民”,而只能是“还富于民”。可见,用“藏富于民”来解读政府与公众的财富关系,实际上是将帝王时期的思维惯性带入共和国中。其滞后性等价于“国王万岁”,但其危害性却超过“国王万岁”。因为喊一声宣泄快乐的滞后口号并不妨碍革命军将国王送上断头台,但是,继续滞后的思维方式则会误导公众对自己权力的认识,从而阻碍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换。
无需深入探讨,“藏富于民”代表着政府对公众的善意,而善意既可给予,也可收回。公众得到了善意,则理当感恩戴德,政府收回善意,公众也无可抱怨,特别是在财富本来就不属于公众的前提下。而在“还富于民”的话语系统中,财富为公众所有,这是公众的权力。政府不能侵犯公众的权力,也就不能占有公众的财富。公众得到财富不必感恩戴德,因为这财富原来就是他们的。所以公众要将一部分财富交给政府,不是这部分财富归政府所有,而只是由政府代管,以便处置公众个人无法处置的事务,这就是公共财政,它不发生财富所有权的转移。如果政府将代管财富的较大部分用于民生,这也不是政府将它的财富放在公众这里,而是将原本为公众所有的财富交还给公众,所以是“还富于民”。而在“藏富于民”中,财富属于国家,公众缴纳的皇粮国税为朝廷和皇帝所有,作为国家财政,与公众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如果朝廷皇帝将其中一部分给予公众,这就是“藏富于民”。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可见,只有厘清政府与公众的财产关系,才能使公众由政府善意的接受者转变成自己权力的维护者,公众就能自觉地监督政府收钱和花钱,从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政府的善意,而是最大限度地遏制官员的贪腐,我国经济才能进入规范有序长期稳定运行的轨道。
对两种提法的比较,不仅是咬文嚼字,更是要在一字之差中找出千里之失,百年不同,从而奠定观念领先转换的基础,促成公民社会改革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