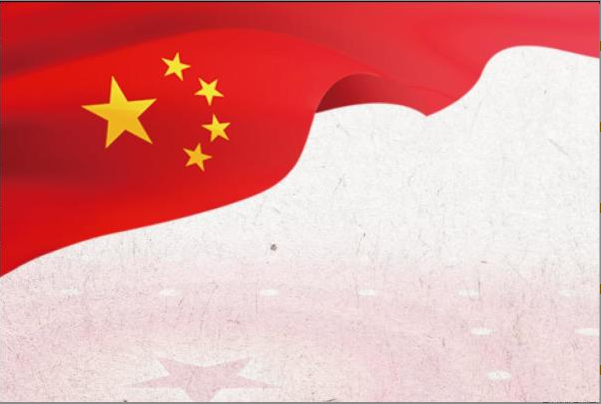FX168财经报社(北美)讯 周一(3月18日),《南华早报》报道称,在过去几周中,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恢复入境旅客和学生数量至疫情前的水平。
当中国一年前放弃了新冠疫情限制并重新开放边境时,人们满怀希望国际学生会回归。2019年,即在疫情爆发前,新生录取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在一年内,这一数字减半了。
一些学生自那时起已经返回,分析人士乐观地认为今年这一数字将会上升,他们指出,新生录取存在时间滞后,航班和学术项目逐渐恢复正常。
但潜在的学生似乎持谨慎态度。他们和在校及校友表示,地缘政治紧张、校园互动、繁文缛节和黯淡的就业前景已经抑制了他们对在中国学习的热情。
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项目执行总监艾米·加德森(Amy Gadsden)表示,随着外国对中国的投资在减少,中国经验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重视。
加德森说:“过去,许多学生希望去中国,学习中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认为这会让他们在就业市场上占据优势。”“这在整个2010年代一直是学生兴趣的主要驱动因素。但现在已经不再如此。”“人们不再觉得在中国度过时间会极大地提高他们的就业前景,而这在15年前还是事实。”
她补充说,对于从国家安全角度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来说,他们必须权衡在该国度过时间的兴趣和担心这可能影响他们未来就业的安全审查能力。
英国籍的杰克·艾伦(Jack Allen),在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完成了为期两年的项目后,表示他所在的同学群体对在中国度过的时间可能成为未来回国就业机会的阻碍存在不同程度的担忧。
“即便在申请之前,我还记得读到一些关于前燕京学者回到美国后被FBI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的文章。”这位25岁的毕业生曾考虑从事公共服务职业道路。
“我在心里也曾担心…我的经历会如何被未来的雇主看待和接受。”
他认为自己“迄今为止还算幸运”,去年7月毕业后,成功获得了在英国商会中国分会担任活动和传播执行官的职位。
艾伦说,但这种风险阻止了他的许多同龄人踏足中国大陆进行学习,其中一些选择了“更安全更简便的选择”,比如短期访问或在台湾的语言中心学习。
他说这种情况是矛盾的。在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时候,有才华的学生却因为担心在中国度过的时间可能会被负面看待而被劝阻获得第一手经验。
尽管尚未公布2022-23学年的官方数据,但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 )估计,2022年中国仅有大约350名美国学生。
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国际教育协会(IIE)提供的数据,这与2011-2012学年约15,000名美国学生的高峰相比,是一个显著的下降。
根据中国教育部发布的数据,国际学生在高等教育机构的新生录取人数在2019年达到最高点,共计172,571人。2020年疫情爆发时,这一数字下降至89,751人,随后逐渐上升至2022年的114,112人。
据中国招生平台中国留学网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考沃德(Richard Coward)称,美国和韩国学生数量的下降幅度最大。
考沃德指出,去年一月中国开放边境时,正值招生周期中段,许多潜在学生已经在没有考虑中国的情况下决定了他们的学习目的地,因为中国在2022年全年关闭,不确定何时重新开放。
“学生平均需要大约八个月的时间来产生初步的兴趣[申请学校],然后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入学,所以存在时间滞后,”他说。
但他对即将到来的9月份的数据保持乐观,因为他表示,兴趣每个月都在逐渐增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贾庆国(Jia Qingguo)表示,地缘政治并不是导致国际学生对中国兴趣下降的唯一原因,因为自疫情后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国家的数量仍然保持强劲增长。
他在两周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年会期间提交的一份提案中表示,对学术界界限的不确定性是外国学生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说,尚未发布有关外国人相关新法律实施的具体规定,“导致了一些混乱”。
例如,他说,与中国最近实施的反间谍法相关的实施细则尚未发布,使得不清楚可以收集什么信息以及如何在不违法的情况下进行收集。
对于在中国进行研究的研究生来说,法律的不明确以及数据收集中的其他困难尤为棘手。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加德森表示,博士生必须找到替代的研究方法,因为中国让数据收集和调查访谈变得非常困难——“所有这些都是学术工作的基石……以前的一代博士生都能够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数据保护法日益严格……所以对于那些希望分析大量数据的研究人员来说,这更难了。开展研究合作也更加困难。”
对于燕京学堂的毕业生艾伦来说,官僚主义是另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特别是在申请工作许可方面。
去年7月,他和他的同学们毕业时,他们有30天时间获得工作邀约,另外30天准备文件,对于一些人来说,这需要回家进行背景调查。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提供比我们入学时已经提供的文件更多的文件,”艾伦说。“在毕业后如此快速地满足所有这些期望非常具有挑战性,需要平衡学习。”
总部位于北京的智库中国与全球化中心的创始人兼主席王辉耀(Wang huiyao)指出,许多国际学生在中国学习所需的各种要素——从航班和付款方式到课程和项目——仍在恢复运营中。
“例如,一个国际项目已经中止了几年,要重新启动它需要重新组建教员队伍并制定新的课程。这需要一个恢复的过程,”他说。
来自巴基斯坦的33岁的安妮·拉加里(Anny Laghari)于2017年在中国获得了MBA学位,她申请了管理科学博士项目,希望能够返回中国。
然而,她现在对是否应该接受一份每月津贴为3500元人民币(486美元)的全额奖学金提供的选择犹豫不决,担心毕业后可能找不到中国公司的工作。
“如果我继续读博士,那将需要五到六年的时间,那时我将会是40岁左右,”她说。
“中国人太在意年龄了——一旦你跨过三十岁,他们就认为你变老了,而且大多数时候由于文化差异他们不太会和外国人相处。”
她补充说,中国经济的低迷意味着即使是年轻的中国工人在就业市场上也面临着严酷的现实,这将使她更难以获得工作签证留在中国。
“我正在考虑所有的原因,我不确定接受这个机会是否会给我的未来带来任何积极的变化,”她说。
“我感觉很糟糕。我真的很想在中国长期居住。我在那里有很多回忆。我喜欢生活在那里。我希望未来对像我这样的人能有一些改变。”
25岁的巴基斯坦籍酒店管理专业人士穆罕默德·沙希德(Muhammad Shahid)目前居住在迪拜,他在一所位于中国西南部城市成都的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上完一个学期后于今年一月离开中国。
“只上课和做作业感觉就像在浪费我的时间,”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的沙希德说。“他们更注重学术方面,而不是技能。没有新鲜事。”
“在课堂上,我们像陌生人一样坐在那里,”他补充道。“我们做了一些展示——但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分开。没有学习,没有分享想法……我对这些事情感到厌倦了。”
他在成都四川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从2017年到2021年期间,他喜欢他在那里的生活。但是当他去年再次前往中国时,他发现学生签证申请比以前更加困难。
“增加了很多要求,”他说。“在中国的移民局,技术方面变得非常复杂。
“中国在技术上比其他国家更先进,但在这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这是现实。”
根据王辉耀的说法,预计前往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将保持相对较低水平,但来自东南亚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
根据《光明日报》去年10月份的一篇文章,超过一半的中国留学生来自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21岁的东南亚东帝汶籍学生盖齐奥·罗萨里奥·里贝罗(Ghezio Rosario Ribeiro)在北京北航攻读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在成长过程中,他看到中国成为国家建设的领导者,这激励他申请到了他所说的“最好的教育”的国家学习。
这位21岁的学生表示,他的国家仍然需要人力资源,特别是在建筑和设计方面。
“我非常乐意在毕业后返回我的国家并在那里工作。考虑到很多中国公司都在那里,我的中文技能将成为我的加分项,”他说。
他表示,即使在解除新冠限制之前,他也享受在中国的生活,但他希望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更高,因为尽管奖学金提供了每月2500元的生活津贴,但他还是不得不打工来支付在北京的生活费用。
据里贝罗介绍,一组超过100名学生签署并提交了一份提案给他们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要求增加津贴。
虽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了一些潜在学生的决定,但许多有过在中国经历的人表示,在中国度过时间的好处超过了消极因素。
燕京学堂的校友艾伦说,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使他能够“抵制对中国的单一化视觉”,并从中国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
加德森指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学生交流,一直是美中关系的基础。“几乎没有问题是没有中国角度或维度的,”她说。“当我们不深入研究和学习时,我们就对自己造成了伤害。”
她说:“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最高级别领导人对教育重要性的表态。”
“需要大学、教师、管理人员、像我这样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去创造机会,并展示并解释为什么去中国以及为什么去中国是有价值的。”